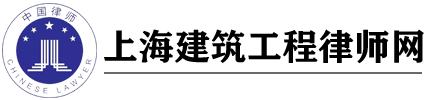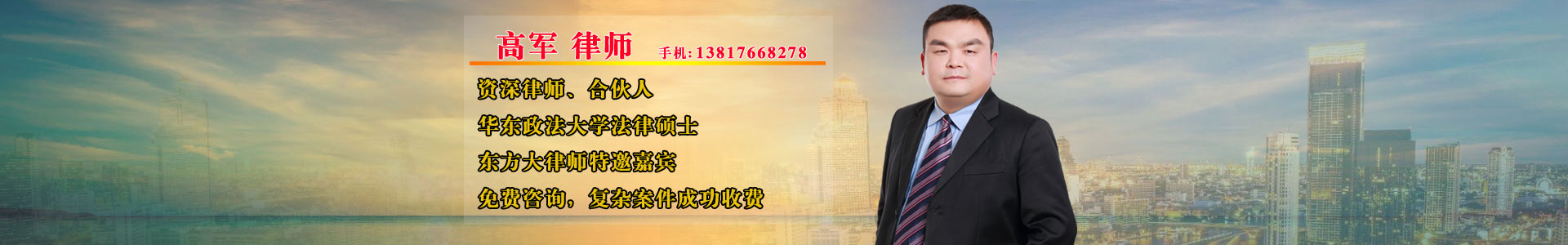本期分享,我们结合一起案例,就自然人C应否构成实际施工人的问题进行分析。
案件基础信息
邓竣、重庆市博海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申3853号】
裁判机构: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时间: 2017年11月15日
各方观点
再审申请人邓竣主张:博海公司在工程中不承担风险,仅借出名义资质,收取管理费,本案是挂靠或转包,邓竣是实际施工人。依据建设部关于印发《1999年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的意见》的通知附件对转包和挂靠进行认定的规定,建设部2014年颁发124号对挂靠经营和内部承包从人、财、物和技术四方面进行区分的解释,综合上述规定和人民法院认定条件,应从当事人是否为建筑企业内部成员,建筑企业对项目工程技术、资金、质量等方面是否加以实质性管理和监督,建筑企业资质要素及财务是否统一管理等方面入手,本案《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中财务管理约定及整个施工过程中,所有资金由邓竣筹措,博海公司在工程款到账后,除管理费、税金、合同约定其他费用后当日支付给邓竣。内部承包是为了掩饰转包挂靠实质。
被申请人博海公司主张:博海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其云南分公司负责,邓竣作为博海公司云南分公司经理,以博海公司云南分公司独立核算方式管理内部承包工程项目。邓竣对外签订与工程有关的合同均加盖博海公司云南分公司印章并落款“云南分公司邓竣”,对内申请用于工程的借款其本人落款均为“云南分公司邓竣”。一审博海公司已经向法庭提交了邓竣社保缴费记录及劳动合同备案登记记录、任职免职文件等,应认定邓竣与博海公司是内部责任制承包合同关系。
裁判观点
关于邓竣是否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问题。
一、邓竣在本案审理中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在本案起诉中,邓竣以自己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由主张工程款并提出享有优先受偿权,其提交了与博海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以及相关为案涉工程借款、出资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实际施工人应当是采取投入资金、材料及劳动力的方式,对建设工程实际进行了施工或者组织施工的一方。从邓竣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看,其并未提交任何与案涉工程施工有关的现场签证、工程验收单证等实际施工或者组织施工的有效证据。
二、其他几个涉及案件中邓竣或者作为博海公司云南分公司代表人或者以该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参与案件审理,但并没有邓竣作为案涉相关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认定。
三、虽然邓竣与博海公司签订有涉及案涉工程的多份内部承包合同,但并不能以此合同认为邓竣即为本案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还应当结合其他有效证据来佐证邓竣是否存在参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的行为。
而邓竣在本次诉讼及再审申请中反复提出其对案涉工程的出资或者垫资行为,既不属于认定实际施工人的直接依据,亦不能够直接认定其具备主张案涉工程的相关款项的资格,故其应以与博海公司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另行主张自己的相关权利。
综上,二审裁定认定邓竣不属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并无不当。
法律分析
实践中实际施工人的类别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转包合同的承包人;二是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三是缺乏相应资质而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的相关内容,实际施工人应具备下列特点:
第一,实际施工人是实际履行承包人义务的人,既可能是对整个建设工程进行施工的人,也可能是对建设工程部分进行施工的人;
第二,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或名义上的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如果直接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则属于承包人、施工人,无须强调“实际”二字;
第三,实际施工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如前所述,转包合同,再分包合同,承包人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合同,承包人支解工程后以分包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签订的分包合同,以及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上述合同中的承包人属于实际承包人;
第四,实际施工人同与其签订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或者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或劳务关系。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释义》规定在认定实际施工人是否为挂靠、是否构成转包时,就要求查明项目管理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同施工单位间有没有合法的劳动合同、工资、社会保险关系。如存在上述关系,则所谓实际施工人参加建设工程施工就属于职务或劳务行为,而非履行承包合同的行为,对外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向发包人、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债权。
上述案例中虽然申请人提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垫资、财务管理等行为,并举出多份内部承包合同,但最高院在认定其是否具备实际施工人身份的过程中更倾向考察主体是否实际施工或实际组织施工,既实际施工人应当是实际履行承包义务的人。否则人民法院可能以其他法律性质认定主体身份(例如内部承包,职务或劳务行为等)
结语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自然人C以“渠道商”+“工程管理”的模式参与项目实施应否构成实际施工人,笔者倾向于认为不构成实际施工人。结合最高院相关论述及案例可知,自然人C并未实际履行承包人义务,而“工程管理”能否认定其实际组织施工尚存争议,而其先行垫资的行为亦不能作为认定实际施工人的依据。
为避免相关风险,站在承包单位B的角度,如须规避自然人C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则承包单位B可与自然人C 签署内部承包协议或雇佣/劳务类协议,将双方法律关系性质定性为内部承包或雇佣;站在自然人C的角度,如希望保有实际施工人身份,则须留存其投入资金、材料及劳动力等相关证据材料,如与案涉工程施工有关的现场签证、工程验收单证等实际施工或者组织施工的有效证据,并且要避免与承包单位签署可能构成劳动人事关系或劳务关系的协议。
上海工程律师